
基层女性的沉默更年
21.1MB
00:0022:59

程学英是趁小孩睡觉的时候跟我通的电话,她跟雇主讲好到阳台上打个电话,宝宝醒了就喊她。
这已经是程学英当月嫂的第六年,无论是育儿技能,还是进入别人的家庭后与雇主一家相处,她都有了丰富的经验。这样的资历在育儿嫂行业正是“当打之年”,属于最抢手的那一批。但从去年夏天开始,她发现自己开始有更年期症状——甚至还是当时的雇主提醒的她,那位宝宝妈妈见她在空调间里还不停冒汗,就对她说:“阿姨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?我妈那个时候也是这样,烦得很,然后冬天还冒汗。”
程学英第一反应是否认。她才47岁,在她印象里,女人最起码到50岁才会开始更年期,过了大半年,对更年期有了更多了解后,她还是倾向于不跟雇主谈论这一点。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去年那位提醒她更年期的雇主算是善解人意了,但自从更年期以来,程学英已经被退单了三次。第一次被退单就是去年刚入冬,在那户雇主家里,别人穿毛衣她只穿一件单衣,又把袖子挽得高高的,都没用,还是忽忽出汗,根本没办法控制。等程学英意识到,人家雇主已经跟公司提了“更换”的要求。站在雇主的角度,她觉得不是不能理解,而且起初她并没有意识到,在她感到烦躁的时候会忍不住连续地说“好烦”,这也加深了不愉快的观感。
除此之外,她睡眠和胃口都变差了。这些都让她精神不振。她自己分析,后来两位雇主要求换人,也跟她的精神面貌变差有关系。
对50岁左右的城市女性来说,更年期和退休是前后脚到来的,这意味着职场压力会减轻,有更多时间和精神关照自己。但对一些基层女性来说,四五十岁,正是她们的“黄金打工年龄”。这个时期,她们往往已经将子女送入高中或大学,一方面得以从育儿中获得解放,形成“空巢期打工窗口”;另一方面,也肩负着一半家庭经济压力,再加上对自己未来养老的焦虑,她们会在四十出头重新进入城市,学习新技能,开始人生中的“中年打工”阶段。
四五十岁的基层男女,进入城市找工作,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女性的工作机会更多。按照农村地区的一些说法,“男的上了岁数,出去当保安都没人要,女的到大城市里做保姆月入过万”。这话虽有些夸张,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迈入四五十岁,男性的体力下降相对更厉害,体力活儿难以为继,假如再遇到疾病或者其他变故,反而需要派出家里的女性去谋生路。
潘女士到宁波一家医院做护工之前,日子一直算是不错。两年前,她家与弟弟家合伙做生意以失败告终,卖掉房子还掉部分债务后,她和丈夫两人商量下来,决定由她出门打工,原因就是她能更快地挣到更多钱。程学英的丈夫六年前得了尿毒症,生活重担立刻压到了她的肩上。我采访的另一位月嫂,生完二胎没多久,丈夫就出了车祸,她只好抛家舍业,跑到省会城市做月嫂。
等她们快50岁,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,正是一生当中赚钱能力的顶峰时期。这也是程学英最懊恼的。她在公司做到第七年,拿最高档工资。趁着这个时候,她工作非常拼。去年,366天她上工了313天,换句话说,一年只休息了53天,有时候单子连上了,下户当天的下午回公司宿舍睡两个小时,晚上接着去下一个雇主家。现在频繁被退单,可以说令她相当沮丧。
城里人盼着退休,农村人到了50岁,觉得工作多多益善。所以退单对程学英来说,非常受打击。虽然领导不会批评她,但她作为一个老员工,面子上也说不过去。同事也会觉得奇怪,程学英向来获得雇主的评价都是一流的,怎么突然被连续退单。但她也不敢直接告诉关心她的人真相,她选择用一些比如“没有眼缘”这样的借口搪塞过去。进入家庭、与家庭成员亲密接触,月嫂群体的更年期变化给工作带来的影响,比其他职业更显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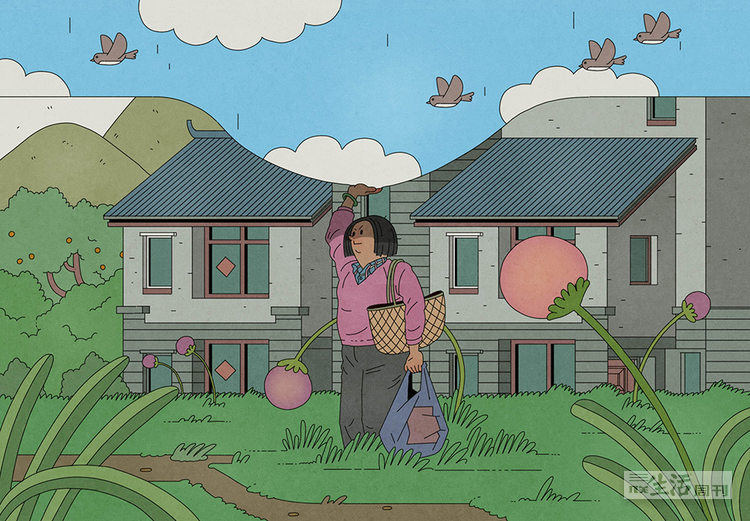
更年期影响的除了生计,还有她们对自己存在价值的判断。刘树琴过去几年就感到非常难熬,原因就是已经在河北老家农村里“闲了七八年”。
刘树琴今年56岁,打从22岁一结婚就没闲过,干活一直干到48岁,突然间就停了。起初在老家是起早贪黑地种地,二十七八岁那年又开始养羊,养了10年,随后去工地当小工。对,一个女人上工地干男人活儿,推水泥、拉车、铲灰,工地之所以乐意雇佣女性是因为给她们的工钱比给男人低。小工一口气干了五六年,她终于换去一个亲戚干的工地上烧饭,算是轻松一点儿了,这个活儿她本来想着能一直做到干不动为止,只是没想这个“干不动”来得这样早。
她跟我描述当时的状态,“身体软了没了劲儿,每天只想在家躺着,就一点儿都不想干了,一点儿都坚持不了了”。出汗,“在那儿待着汗就顺着脖子往下流”。而且还心烦,“光想上街找个偏僻的地方去大喊大叫”,虽然也没去。她说最多就是在家哭一阵,能稍微好点儿。但从此干活儿是一点儿都不想干了。
刘树琴很纳闷儿,干了一辈子活儿,怎么突然就啥也不想干了。家里倒是没人指责她,甚至还带她上北京看过病,医生让她做些检查,她没舍得花那个钱,实际上也不太相信“抽血能治好不想干活儿的毛病”。回到村里,整天在家闲着,心里就想,五十来岁,年纪轻轻,就啥也干不了?“有时候想想这个就觉得活着没意思”。
假如刘树琴当时能舍得在北京的更年期门诊做些检查,医生会告诉她,这些症状并不神秘,它们只是雌激素水平下降的表现之一。雌激素对女性的保护涉及泌尿生殖、心血管、骨骼、神经以及皮肤、毛发等多个系统。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5年发布的周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,40~60岁中国女性中,有46.3%的人报告出现了更年期症状,其中失眠(50.0%)、疲劳(48.2%)和焦虑(46.9%)是最常见的三种症状。“这些症状不仅影响身体的舒适度,还可能对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。”
不光是刘树琴不舍得花这个钱。就像一位基层医院的妇科大夫说的那样,“她们有些人连饭都吃不上,哪个会管更年期。除非是症状比较严重了,才会来我这儿看看”。四川省什邡市妇幼保健院更年期门诊曾英主任告诉我说,她接诊的农村病人,促使对方来看门诊通常有两大常见症状:一是潮热出汗失眠,晚上睡不好觉影响她白天劳作;二是性生活困难,“50岁左右这个人群,一般都要出去打工,年末春节回来夫妻相聚,但绝经后一整年都没有性生活,突然要进行是很困难的”。
但是,在农村地区,即便想看更年期相关症状,也无法就近在乡镇卫生院解决,这儿的医生要么没有完备的更年期相关知识,即便有心为对方开激素类药物,也面临着药物不全的困境。我在小红书上碰到一位年轻女士,她告诉我说,她妈妈出现了更年期大出血,到县医院挂急诊,给出的解决方案是“做刮宫手术”。直到她回家带她妈妈去市医院看,才知道原来可以采用补充雌激素这样的方案来应对。
刘树琴没有走到补充雌激素这一步,即便走到了,按照北京市某郊区妇幼保健院一位主任医生的经验,很可能也坚持不下去。雌激素得长期服用,但是因为医保限制,比如替勃龙这款常用的雌激素,一次只能开一周的量,“病人每周都得来一次医院,而农村病人可能来一趟要换两趟车”,能这样坚持的农村病人屈指可数。
无论如何,在刘树琴这儿,她已经将自己判为“没用的人”。

过去将近30年,刘树琴种地、养羊、做工地小工,三种高强度劳作让她强烈依赖自己的体力,更年期带来的症状不仅让她失去了生产工具,也让她的社会角色骤然失效。如果说大城市更年期女性面临的是一种衰老后容颜不再的外貌焦虑,基层女性的焦虑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,她们很少顾虑到“老了、不美了”,或者“更年期意味着失去性魅力”,她们直面的是一种更为紧迫的“存在危机”。
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其实是在呼吁身体休养,但基层女性又恰恰如此依赖自己的体力。这种矛盾状态让她们无所适从的同时,产生强烈的危机感。
程学英前一阵得了一次急性肠炎,与此同时还有泌尿感染,原本第二天要上户,“不得已”休息了几天。那几天里她说自己蛮焦虑的,她隐隐约约感觉到,这一行或许自己马上就要做到头。几乎是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,她在休息的时间里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问题,好多思绪在头脑里打转。她平躺着,感到有点胸闷和压迫,可能是前两年得了肺部疾病的后遗症(注:实际上大概率也是更年期症状);失眠,过去一挨枕头就睡着,现在总要熬一会儿才能入睡;头晕,可能是缺觉的缘故;腰不好,长期带宝宝换尿布,腰疼是逃不掉的。这些问题里,哪些是更年期引起的,哪些是疲劳引起的,程学英搞不清楚。好像也没工夫去搞清,思绪很快就被焦虑占据。
她最大的焦虑还是这份工作还能干多久。跟雇主家面试时,她最害怕的问题是,“您这个岁数,会不会精力不济”。虽然公司教给了她们应对话术,但她打从心底里认为,精力不可能比得过年轻的同事。
不止一位月嫂告诉我说,她们已经看到了月嫂这个行业在“年轻化”,她们刚入行的时候,起码也是40岁,“现在已经有30多岁就出来当月嫂的了”。
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打工,月嫂、家政工和护工是较为常见的去向,事实上,这几个工作都是传统上女性角色职责的延伸,它与家庭内的母亲、妻子、女儿(儿媳妇)的职责高度重叠,是一种“母职的市场化”,这就意味着她们不仅要提供技能,还要付出一定程度的“情感劳动”。雇主对一位月嫂的最高评价是“照顾宝宝像照顾亲生小孩那样用心”,同样的,老人对护工最好的评价也是,“就像自己的亲女儿一样体贴”。
从赚钱养家的能力这个层面来说,完全可以将上述群体称为“职业女性”,但家庭内部,对她们的要求很可能就是,随时放下工作,回老家服务家庭。对月嫂邓姐来说,正是因为已经是“职业月嫂”了,照顾儿媳妇的月子恐怕就更是当仁不让。邓姐去年“十一”假期刚刚给儿子办完婚礼。她老家在湖北洪湖,婚礼酒席的习俗是连办三天。最终,邓姐摆了三天半流水席,一天两顿,平均每顿有10桌,花去她10万块钱,再加上22万元彩礼,一场婚礼共计支出32万元,这几乎是她干月嫂三年的收入。她告诉我说,办婚礼前她就跟儿媳妇许诺,现在假如不急着要孩子没关系,到时候坐月子包在她身上。她还说,“假如到时候你们嫌弃我年纪太大,我就在公司里找个年轻点的姐妹来做,我负责采买一日三餐和做饭”。在她的叙述中,这些就是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。
就说刘树琴,虽然她自认为赋闲在家七八年,却也在“烦躁得不想干活儿”的更年期,照料了女儿两次月子。女儿嫁到山东,但是婆婆身体不好,第一胎女儿回了河北老家生产。二胎决定在山东生,刘树琴又奔过去照顾。那段时间她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,但为了女儿还是耐起性子,“洗尿布洗了40天,烦得很,但我不做谁做呢”。

家政阿姨李大欢是我所有采访对象当中最能干的。她今年55岁,她首先让我吃惊的地方是她的收入,她说她一个月能挣1.7万元。这是我在我们小区一位邻居家里碰到的采访对象,吉林人,身高一米六三,体重120斤,说话做事干脆利落,雇主对她的评价是“不服不行”。
周一到周五每天干四家,礼拜天说是休息,但还是要干三户人家。平常都是早上6点钟出门,晚上8点回家,礼拜天下午三四点钟收工回家算是一周唯一的放松时间。现在的时薪能有45到50元,这意味着李大欢一周工作时长多达90个小时。
李大欢跟丈夫二人双双到北京打工,到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。两夫妻年轻的时候一起做过小买卖,租过菜摊,做过烟酒店,最后双双干了小时工。丈夫是送快递、送外卖,她开始做家政。大约10年前开始,她的收入就超过了丈夫。去年年底,丈夫生了场病,需要静养,从此就回了老家,说不想再回北京了。按李大欢的说法是,她老公挺娇气的,在北京这么多年,她在别人家里做完家政,回到二人的出租屋里所有的活儿也是她干。现在回了老家一个人生活不到半年,已经喊她回去了三趟。最后一次,她回去雇了个人照顾他,又过渡了几天,才重新回到北京。但她老公抓住机会就会劝她,一把年纪了也回家得了,“赚多少钱是个够啊”。
李大欢觉得不够。虽然她现在有时在雇主家里,洗着洗着衣服会感到非常烦躁,衣服一甩就就从卫生间里跑出来了,但这些雇主都是十年以上的老雇主,十分依赖她。“就比如我这趟回老家,一回就是半个月,小时工不哪里都是?都是每天要用工的家庭,但他们都说等着我回来”。
李大欢更多的焦虑或许来自价值感丢失。亲戚朋友都知道她在北京一个月能挣1.7万元,大家都夸她“能干”。她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,当一个无用的人。李大欢是从行情价10块钱一小时干起的,十几年过去,干到现在是四五十元一小时。她基本不会写字,只上到小学二三年级,她说:“我这样的,能在大城市站住脚,很不容易你知道吗?”
“所以现在要是放下的话,确实有点不甘心。我从早到晚骑个小电摩托,一干上活儿,也没感觉说哪疙瘩不得劲儿。但是回老家,要在农村还好点儿,现在是市里头的楼房,现在天暖和了,晴天老日地就这么一蜷,真就有点儿焦虑了。”
不管是远离家乡到北上广打拼,还是就近到省会城市打工,这一代农村女性恐怕很难摆脱“别人的看法”。30年前,王传霞一家四口从农村到省会石家庄打拼,除了3岁的小孩,还有新近没了丈夫的婆婆。
打过各种零工,41岁的时候,王传霞得以在一家医院的餐厅稳定下来,因为总算是待遇还不错,节假日加班都有双倍薪水。她在厨房的工作需要早起,5点钟无论如何要从家里出发了,早餐供应到8点半,说是有休息时间,其实也马不停蹄地需要开始为午餐做准备。下午1点钟下班,回到家里虽然总是非常疲惫,但最多也就能眯着个半小时,再要睡觉也得等到晚上了。家里大小事务都是她在做,老的卧病在床,小的上高中,丈夫有时两三个月不回家,一回家能住半个月——但还不如不回来,是“双脚往茶几上一搁,等着吃饭”的那种男人。
王传霞说她这辈子也没指望男人能给她做一口饭吃,“哪怕熬一口粥”。那两年累到什么程度?她说,“每天早上只要能睁开眼就得往外冲”。现在已经过世的婆婆,在她人生最后两年,对王传霞依赖性非常强,半夜二人同住一屋,有个风吹草动,起身照顾的人总是她。有时候还在医院餐厅上着班,电话就打过来了,说哪里哪里不舒服,要上医院去。王传霞找这个半天的班儿上,大部分原因也是婆婆这身体,“老太太觉得你回来好像她的心就安定了”。
47岁那年,王传霞开始有更年期症状,而且严重得让她很不适,“我有个姐姐,她(更年期)几乎没有什么症状”。不过她身高只有一米四五,不到100斤,天生饭量小,而且不爱吃肉,她认为可能是自己体质本来就不好。回想婆婆过世前最后两年,王传霞还会感慨,自己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更年期让她睡眠变得非常差,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,婆婆长年服用安定类助眠药物,这药对她来说是唾手可得,但她从来没碰过,她的观念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吃药。与其吃药,不如忍耐,她说,“要论个子,人家都觉得我吃不了苦”,仿佛一旦借助药物入眠,就与“不能吃苦”画了等号。但长期失眠,高强度的厨房工作,贴身照护婆婆,这些都证明了这个“别人以为吃不了苦的女人”的吃苦能力。
她丈夫是家里老小,但因为农村的习俗,他们结婚后一直没分家,所以两位老人的赡养责任都在他们夫妻身上,公公去世后,丈夫拖家带口领着老娘来到市里,说不想让老娘吃苦,打从一开始,他们就租的是楼房。十几年前,夫妻俩用小半生的共同积蓄在市里买了房,婆婆的生活条件再次得到加强。无论是时间、金钱还是情感,方方面面,对老人的赡养和照护重任,几乎完全是王传霞这个儿媳妇承担的。
王传霞今年57岁,婆婆过世已经是八年前的事,但突然病逝那一天的细节,她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她像讲故事一样仔仔细细跟我复述了一遍,所有人(包括她老公在内)如何惊慌失措,面对医生如何一问三不知而只有她知道所有用药情况,而她又是如何没掉一滴眼泪地料理了所有的后事。语气里是有自豪的,听得出来,这应该是跟不少人讲过许多遍。她说,婆婆走后,她最大的感受是“空落落”的。反复讲述婆婆临终那天的场景,是她在努力消化这种无力感。这种讲述或许也是一种乡土智慧,过去她是凭借孝顺获得尊重的,现在,这种尊敬不应该随着婆婆去世而消失。
令她欣慰的是,每次她们回老家去,她丈夫的哥哥姐姐对她总是挺尊敬,虽然是老小家的媳妇儿,但她感觉大家待她就像是对待大嫂。走在村里,也总是“很抬得起头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