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原创 第二新闻中心 新新报NewTimes

40岁的中年女性,面临着很多改变:身体机能逐渐下降,雌性激素分泌减少,疲惫和衰老似乎来得更加轻易。
与此同时,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丝毫不减。抚养子女,照看家庭,平衡工作,她们“被生活填满了生活”。除此之外,迈向中年的她们还多了一项任务——保持情绪稳定。否则极易招来“是不是更年期了”的戏谑。
苦闷、不安全感、痛苦和释怀……种种情绪交织而成她们复杂的世界。
40岁女性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?在40岁这个不惑之年,她们的人生又何以“不再稳定”?
本次报道将聚焦3位40岁+的女性,试图寻找她们内心深处那些更加隐秘的变量,以及引发改变的火苗。
采访 | 邓子奇
撰稿 | 郭佳莹 郭艾昕 杨楠
内容编辑 | 郭佳莹 邓子奇
新媒体编辑 | 杨楠
出品 | 新闻工作坊·第二新闻中心

10个未接来电
在家里其他人眼中,李丹丽就像一个小哪吒,风风火火、我行我素,但又总能在玩笑和打岔间就将大大小小的家庭矛盾徐徐化解。
而在老一辈眼中,李丹丽有些“疯癫”,无论旁人怎么闹她、骂她,她都面不改色,接着就能在饭桌上若无其事地吆喝着让大家吃饭。
面对她,就像蓄力的一拳打在棉花上,表演出的圆滑让你永远使不上劲儿。
兄弟姐妹都是攀钢体制内的职工。在那个“吃上公家饭”相亲都高人一等的时代里,李丹丽有闯劲,敢经商,是家里出钱最多的人。在重男轻女家庭里,她被忽视着长大,却能为父母置办房子、勇闯天涯。既不顺从,也不服输。
紧紧包裹着她的,是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和漫不经心。
但面对女儿小何时,李丹丽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。
小何清楚地记得,那是一个距离研究生考试不足六个月的午后。撑不住昏沉的睡意,她趴在桌上小憩了半小时。撑起身子拿过手机,小何懵了。满满一列来电信息已经占据整个手机屏幕,新的消息还在不断弹出——10个未接来电,来自妈妈;无数未读消息,来自微信群聊。
“宝贝你去哪了?急死妈妈了!”
“再不回复妈妈,妈妈要联系你班主任了!”
“小何妈在找她,她在宿舍不?”
“你妈给我打俩电话了!”
“给我也打了!”
从几个零星跳出的关键词中,小何大致拼凑出事情的原委。“在我睡着了5分钟后,我妈刚好在微信找我,过了10分钟,她就觉得我出事了。”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奈,“我只是不小心睡着了半小时而已啊……”
小何很快给妈妈回电,安抚好她惊恐的情绪,接着在微信给被打扰的朋友和同学说明情况、一一道歉。小何对妈妈打扰到自己周围人的行为感到尴尬,但同时,她又为妈妈感到心酸,因为她明白,这种情绪的爆发不是妈妈能够控制的事。“所以我就只能给她发个抱抱的表情,然后把她晾在那里。”
“你妈怎么比你还感性”,朋友打趣,小何只能在群里无奈又戏谑地回复:“抑郁妈带不出开朗女。”
小何觉得,“妈妈有些病态地依赖着我”。初入校园,李丹丽会第一时间要求得到小何舍友的联系方式。每当小何转发社会新闻到朋友圈,李丹丽总会哭着打来电话,求小何删掉,原因是“妈妈怕你有危险”。而无论是睡觉、学习还是外出,隔一会儿不看手机,小何的手机上就会多出几个未接来电。

来自妈妈的电话 受访者供图
不是没有尝试过和妈妈沟通。但每当小何挑起话头,李丹丽只会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小何的脸色,以一种卑微而妥协的语气辩解,“妈妈只是因为担心你才这样,妈妈不能没有你”。小何无法再对着这样姿态的母亲说什么,只能一点点地将原本想说的话咽回肚子里。
李丹丽对小何的依赖更像是由多种情绪叠加而成的。
一方面,这源于她对小何负罪感般的愧疚。她总是自卑于自己出身的贫穷,认为自己没办法给小何提供更好的生活,生怕小何在家境更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。
另一方面,小何觉得自己身上也承载着李丹丽对未出世双胞胎的复杂爱意。在与小何的爸爸相遇之前,李丽丹结过一次婚,还怀了一对双胞胎。但面对孕期家暴的丈夫,她毅然决然地打掉已经成型的6个月胎儿,并选择离婚。
“她经常想起来她有个双胞胎孩子,我觉得她可能把那份爱也给到我身上了,本来我是一个孩子的爱,她可能把三个孩子的爱都给我了。”
又或许是父母对李丹丽成长的忽视和缺失,让她在满不在意的皮囊下深埋了一种怨怼后的释然。这种成长上的缺失也化作身为母亲的多愁善感,更加变相地弥补在了小何身上。
与很多家庭的“催婚催生”不同,李丹丽不希望小何走她的“老路”。“她太依赖我了,太病态的那种。她心理一直亏欠着,对我的这种依赖也会折磨她自己。她怕我也陷入到和她一样对孩子的愧疚和痛苦中,所以她不想让我要小孩。”
近些年经济不好,李丹丽没有继续外出经商,而是回到老家攀枝花做起了个体户。她没有什么固定的生活轨迹。小何不在身边的时间里,李丹丽和丈夫的生活方式更贴近在大城市周末休息的年轻人。也许睡到中午才起床,乐意做饭的时候随手买点菜炒炒吃了,犯懒了就吃速冻食品。用小何的话来说就是:“两个人烂在家里。”
在北京读研的日子里,小何时常被依赖自己的妈妈和自己预想中的未来规划拉扯着。李丹丽想让她毕业回到家乡攀枝花陪在自己身边,但小何还有自己的野心。“她还是想让我在她身边的”,“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,因为有妈妈在的原因,我会觉得没办法做很多事。”
李丹丽对小何看得很重,却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。
她会向小何发一些小牢骚:“哎呀,现在我们在这里活得好没有意义呀。”她偶尔也会豁达地告诉小何:“如果以后有什么疾病需要一直被照顾,那么那个时候就可以让我死了。”
小何说:“她真的太爱我了,但其实我更想她多爱她自己一些。”

阁楼上的“疯女人”
与小何妈妈相同,小何的二姨李英同样是家里不受宠的孩子。但有所不同的是,李英已经离婚多年,她唯一的儿子却并不像小何那样能够理解自己的母亲。
在小何眼里,李英的性格不太讨喜。她倔强,认死理,不低头,“她有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感觉。你打她,她不认输,她要跟你对着干”。外公外婆不喜欢李英,家里的其他成员不喜欢李英,就连曾经的小何也不喜欢她。
但当小何渐渐长大,知道了那些发生在李英身上的往事后,她对李英的情感变得不那么一样了。
李英的人生曾有一个偶像剧般的开场。她在十七岁的青春年华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恋爱。然而好景不长,这段关系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,她被锁在家里两个月,父母禁止她再与对方见面。
但生活不会总如影视套路那般发展,这段恋情终究没有继续下去。更像是一场闹剧,再见面时,对方已经要结婚了。“她觉得很恨,既恨自己的父母,也恨那个男人”,而就是从那时起,“她不再相信父母,也不再相信爱情了”,小何说。
不再向父母反复强调自己“要义无反顾追求自由和爱情”,李英开始接受“父母之命”,接受相亲。
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,李英认识了一位大她14岁的男人。很快,李英嫁给了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男人,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。
相亲、结婚、生子。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中式家庭里长大,李英做到了父母对她的一切规训。
但李英的婚后生活并没有如父母所愿,走向幸福和平静的坦途。结婚不久后,丈夫就暴露出好逸恶劳的品性和嗜赌的恶习。那个不着家的男人,在外打牌喝酒彻夜不归,对家里发着39度高烧的儿子不闻不问。一桩桩、一件件,压在她身上,重若千斤。李英在婚姻中长时间承受的憋闷,终于在儿子高考的那年爆发。
“我感觉她更年期就慢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”,小何推测。
无爱的家庭不仅折磨着母亲,也逼迫着孩子走向沉默。李英计划离婚的那两年,正读高中的儿子对什么事都不在意。即便后来得知李英确诊了乳腺癌,他也依旧不闻不问,甚至连个电话都没往家里打。李英试探性地告诉儿子自己想要离婚,儿子只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,“你想离就离,跟我没有关系”。
儿子的态度虽然冷漠,但姑且算是支持,李英的父母却对此坚决反对。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理由:李英本来长得就不好,脾气也坏,人又到了中年,离了这个,下半辈子很难再结婚了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担心离婚会对孙子的高考升学造成影响。
前是对自己不予支持的父母,后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儿子,难以忍受的家庭是压在李英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段日子,李英的情绪一触即发。要是有旁人在她面前若有似无地提起离婚、孩子之类的话题,她的脸会立马拉下来,以一种恶狠狠的眼光觑着对方,直到对方闭嘴。李英铁了心要让家人同意自己的决定,家里一点无关痛痒的口角总会被她的不依不饶升级为一场“战争”。
最后,或许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堪其扰,李英终于如愿以偿。父母默许了她的离婚。
即使摆脱了婚姻的枷锁,李英似乎依然被禁锢在牢笼里。
从小到大,她几乎从未得到过来自父母的关心。在李英心里,父亲把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当成自己的孩子,唯独只当她是家里的一个保姆。这种不满长年累月地积压,在无声的对峙和冷战中生根发芽,逐渐演变为更剧烈的冲突。类似的情节每隔几天就要在家中上演:总是以父亲的冷言和李英的呛声开头,再以互不退让的争执和对骂续接,最终以李英摔门而去收场。最严重的一次争执中,李英憋着通红的脸,两只眼睛死死瞪着喘着粗气的父亲,然后撂下一句“你就算死了,我也不会给你流一滴眼泪”。
儿子工作后没几年,李英的弟弟有了个女儿,也就是李英的外甥女。由于弟弟和弟妹白天都有工作,李英的双亲又年事已高,一家人商议后,决定雇李英来带女儿佳佳,每个月按时给她发工资。
于是,李英与这个本就不算亲近的家之间又多了一层雇佣关系。
她渐渐感觉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存在。每逢过年过节,一家人总是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,吃着团圆饭,大笑着说些吉利话。而李英总是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,她与餐桌和客厅的热闹隔了一层厚厚的壁障,仿佛她本就不属于这里。
佳佳的出现,仿佛是黑暗矿洞中的一道光亮,让李英不顾一切地想要抓紧。

李英给佳佳扎辫子 受访者供图
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,再到步入学堂,李英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佳佳。她照顾着佳佳的一切饮食起居,在心里偷偷认领了母亲的角色。只有她们两个人在的时候,她让佳佳喊她“妈妈”,自己喊佳佳“女儿”。“是更喜欢生你的妈妈还是我这个妈妈?”李英总是一遍遍地、不知厌倦地把这个问题抛向佳佳,并且,渴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
除了最亲密的身边人,李英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这两年,李英开始迷上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从前的她很排斥使用社交平台,固执地认为“用朋友圈的人都很傻”。但现在,李英几乎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最新生活分享到朋友圈。与此同时,她也开始学着打扮自己——买自己以前很少买的裙子,每天在镜子前认真梳过两遍头发。她还联系起了昔日同窗的老同学,主动与小区的同龄人搭话,跟着学跳广场舞,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子,认识新的人。
被挤压在家庭生活的缝隙里,李英正努力寻找着属于她的更广阔的空间。

她睁开了双眼
“不想上学……”暑假接近尾声,而这已经是女儿周琪第四次喃喃自语了。
杨好再也忍受不了了。送走返校的女儿后,接连几天的晚上,一想起这件事,杨好整个人止不住地发冷、发抖,“心脏一抽一抽地发疼”,她坐在床上紧紧地环抱住自己,企图汲取一点温暖,但眼泪还是不断落下。整夜整夜,杨好始终难眠。
大概是近几年开始,旁人的只言片语总会在杨好的心里引起湖面涟漪般的连锁反应,她无法控制地陷入过度思考和情绪内耗。然而,比起涟漪的轻盈,这次的情绪更像是狂暴的漩涡,她感到自己正在被席卷、被吞噬。
女儿无意间流露出的恋家和不舍让杨好感到一阵触电般的惊恐,她断定,这是女儿不独立和缺乏自理能力的表现,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自己——太无知,太缺乏关于教育的理论知识,以至于养育女儿时只靠陌生的惯性推动。
但周琪觉得,杨好这份偏执到几乎有些过激的愧疚,要追寻到杨好的少年时代。
杨好45岁了。在她的印象里,抚育了五个子女、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,在家里有着说一不二的威严。
杨好至今仍记得,中学时,她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约定各自买辆自行车,相伴骑车上下学。放学到家,她顾不得放下肩上的背包,快步来到父亲跟前,略带不安地提出购买自行车的请求。一向温和的父亲是家里最疼爱孩子们的人,稍稍询问了几句,便笑着应允了。杨好还来不及露出欣喜的表情,坐在不远处的母亲就迅速起身,“你总是这样,看到别人家有什么,自己就想要,怎么会这么虚荣?”“读了书也不懂体谅父母,没用的孩子,滚出去!”劈头盖脸的责骂声传来,杨好僵在原地,一声不吭,只双腿微微颤抖着。
回想起那时的情景,已为人母的杨好仍会下意识地用手轻抚自己的胸口,深呼一口气,语气中有一点无助。时隔多年,父亲在那一天穿的衣服、母亲在那一天扎的发髻,都已经在回忆中渐渐褪色了。唯有母亲因极度愤怒而扭曲得有些陌生的脸,在杨好的心中凝结成一个永恒的缩影。
“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。我想,或许我真的做了很坏很坏的事情。”
于是,在此后漫长的三十多年里,杨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她习惯于时时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,下意识地察言观色,尽量避免人际交往中任何造成不愉快的可能,甚至讨好身边所有人。她以这种方式小心翼翼地构建着属于自己的安全感。
因此,在面对女儿时,杨好绷紧了神经,时刻警惕着自己儿时经历的再现。她给予了孩子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自由——除了原则性问题,其余要求她都尽力满足。
然而,当已经20岁的女儿流露出对家的眷恋和不舍,她心里的大厦在顷刻间崩塌了。在旁人眼里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事,却被她认为是女儿性格上的缺陷,而这一切的源头又总是归咎到她自己,她陷入无限自我苛责的死循环。杨好的脑子里像有几千个喇叭在同时说话,一些喇叭在指责她的无能,一些喇叭在嘲笑她的无力,一些喇叭甚至播放出母亲尖厉的声音——一遍一遍地放送着儿时母亲责骂她时所说的那些话语。
为了转移注意力,杨好连着刷了好几天的“小红书”。大数据似乎也探测出她的情绪,主页上,充斥着各种静心、修心、教育相关的笔记。一条短视频让她停下了下滑的手指,视频里,一位老师语气温和,讲述着低落的情绪从何而起。“放情绪一条生路,情绪也会放你一条生路”——一行文字说明附在最下方。
杨好感觉自己被击中了。她一口气看完了作者主页的所有视频。没有多少犹豫,杨好点开了与作者的私聊界面,将自己的困惑和痛苦一股脑倾吐而出。不久,对方回复并邀请杨好加入了她们的微信群。这是一个“情绪共修”群,群内78人,多为三四十岁的女性。这个群更像是她们的自留地,当工作、生活中发生了不顺心的事,她们会选择在这里倾诉。
此后,杨好开始寻找更多类似的组织。通过关键词搜索,她找到了一个名为“舞修行”(化称)的活动组织方。在他们发布的视频里,五六名中年女性穿着宽松的白色纱袍,随着悠扬的古筝声缓缓舞动着。杨好盯着屏幕,幻想自己也身处其中,如一枝轻盈的柳枝,在春风中静静地摇曳。杨好感觉自己得到了久违的平静。
今年国庆假期,“舞修行”在东莞组织了一场线下交流活动,包括杨好在内,共有数十人报名参加。杨好格外期待这次活动,提前三天就开始收拾行李,始料不及的是,活动由于疫情原因被迫取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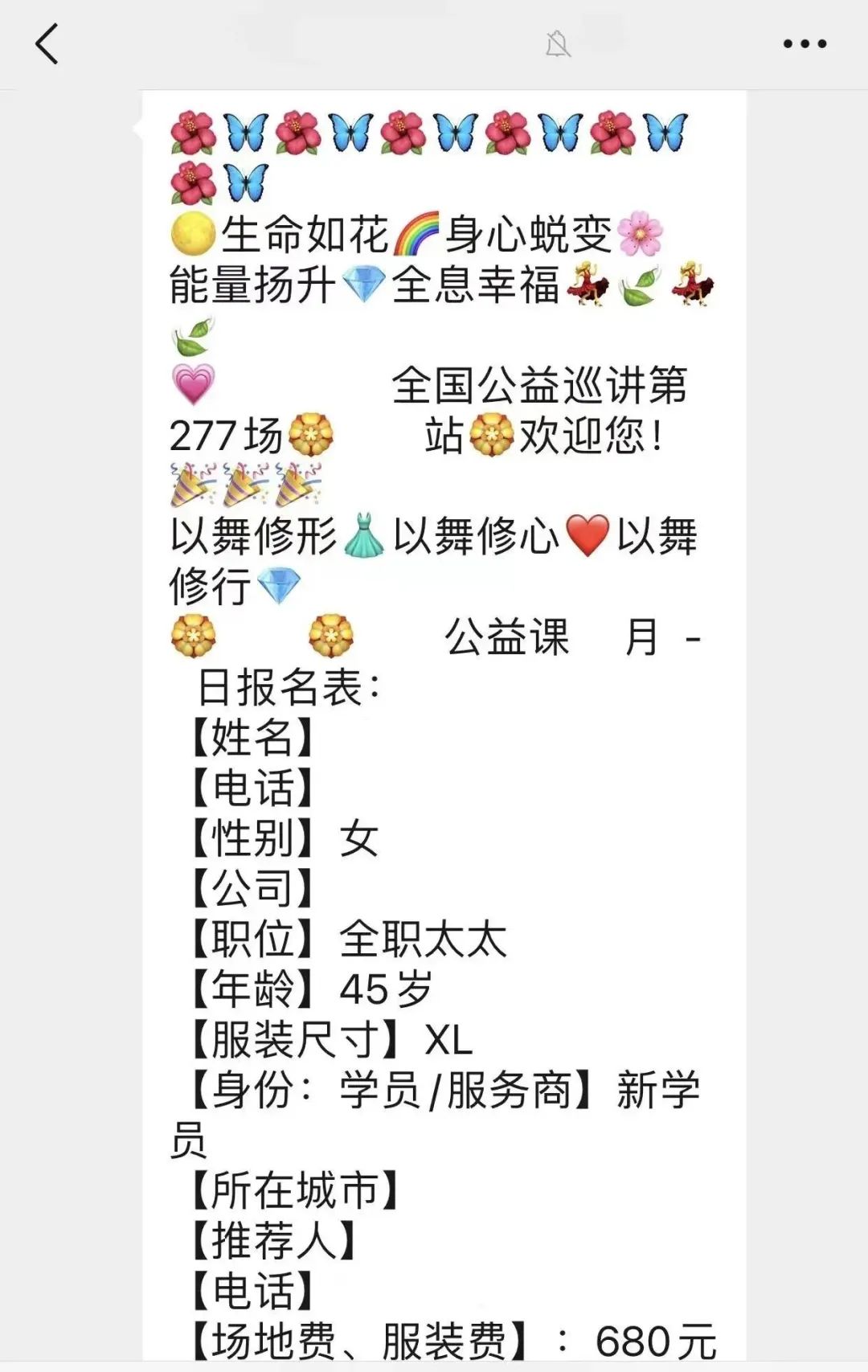
线下交流活动报名 受访者供图
活动没了,杨好有些恍惚。七天假期,她不用再像平时一样接送儿子上下学,也不用到公司坐班,一向固定的生活秩序被打乱,杨好的心再次被一种莫名的惊恐绑架。不同于以往,一向不愿意麻烦他人的杨好终于开口向丈夫寻求帮助,“我好像感觉不到活着的意义了”,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为了缓解她的不安,第二天,丈夫驱车带着杨好来到了郊外乡下。
摇下车窗,杨好静静地看着飞驰而过的街景。车开出市区的那一瞬间,窗外扑面而来的风打在她的脸上,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,“我突然感觉我一下就好了,真的,一下就好了。但是那一刻,我突然感觉,我的心被囚禁得太久了,真的太久了。”
从乡下回来后,杨好变了很多。为了掌控自己的内心,她决定做点什么。杨好买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,准备心理学咨询师考试;开始学习冥想,坚持每天跑步。她努力尝试达成自洽,靠自己抚平内心深处的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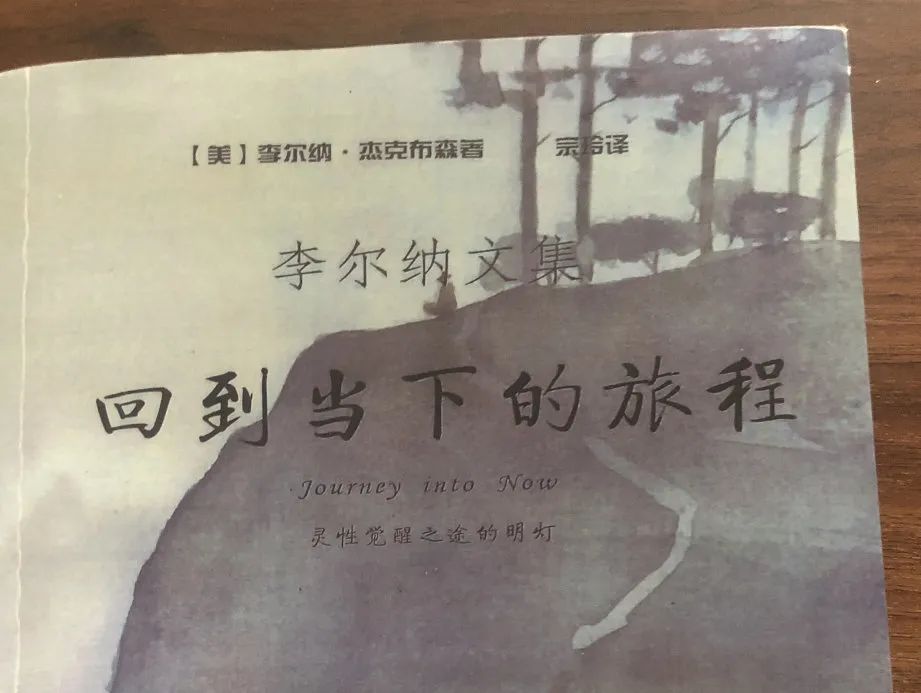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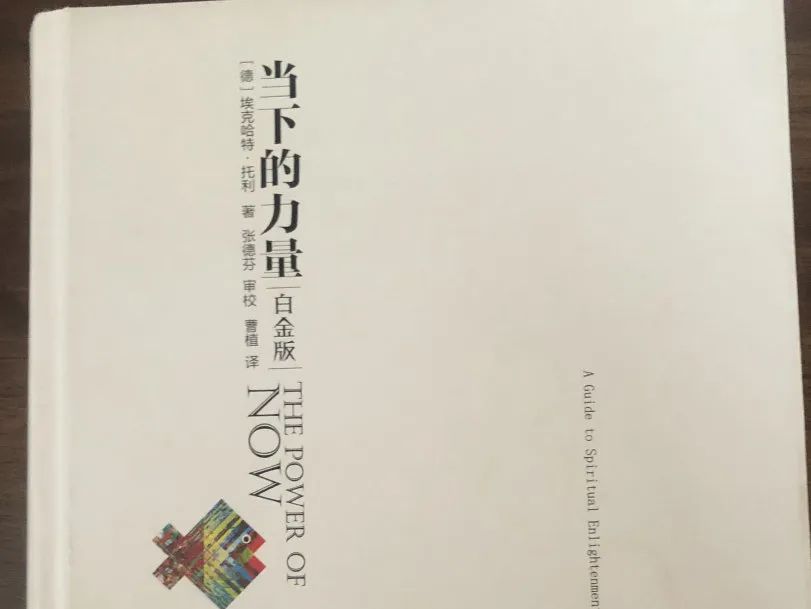
杨好在读的书 受访者供图
杨好也尝试和母亲谈论自己儿时的创伤。一个失眠后的清晨,杨好鼓起勇气敲响了母亲的房门,说起了自己最近的不安与焦虑。母亲没有不解和指责,杨好于是继续讲起了自己童年的创伤,聊到那辆她未曾拥有的自行车,还有记忆中母亲数不尽的眼泪。那一刻,两人都各自落泪。这之后,母亲每隔几天就要问起杨好的身体状况和睡眠,生怕她又陷入牛角尖。“我想,我真正感受到了母爱”,杨好语气有些释然。
杨好还开始强迫自己不再太在意别人的眼色。她开始学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,家里的饭桌上不再只有丈夫和孩子喜欢吃的菜,也开始频频出现她爱吃的海鲜。最近,杨好还报名了旅行团。不出意外,杨好将在下个假期独自和一群陌生人前往长白山。
回忆起去往乡下的那天,杨好脸上露出了笑。在车上,她和丈夫二人都静静地感受着面颊旁肆意流淌的风,没有人说话。音响里,许巍的《蓝莲花》播了一遍又一遍。
穿过幽暗的岁月
也曾感到彷徨
当你低头的瞬间
才发觉脚下的路
心中那自由的世界
如此的清澈高远
蓝莲花
汽车穿过隧道,杨好睁开了双眼。

更广阔的世界
这些只是李丹丽、李英、杨好生活的一个侧面。
放眼更远的世界,许多中年女性行为或精神上的不稳定被视作更年期的异样,更多的女性正遭受着更年期的污名化。周琪同学的妈妈,在今年秋天变得更加多愁善感,却被丈夫调侃“更年期到了,别那么矫情”。似乎人到中年,便丧失了拥有情绪的权利。但事实上,更年期并不独属于女性,更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拥有的生理阶段。
在某种程度上,“不稳定”意味着改变。用“更年期”等宽化的概念掩盖中年女性的精神困境,无疑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霸凌,或刻意或无意地扼杀她们摆脱精神困境的可能。
但日子还要继续。
李丹丽和朋友相约去外地旅游;李英穿上新买的漂亮裙子,认识了更多的人;杨好还在尝试着报名新的线下活动。
无论如何,她们40岁的人生,至少比过去更广阔了。
(文章涉及人物、机构均为化名)


原标题:《聚焦 | 3个女人“不稳定”的40岁》